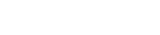“本地生活”戰端終局
互聯網時代,流量就是經濟,為流量尋找合適的變現路徑才能使平臺型的商業模式形成閉環。流量變現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廣告,而廣告的模式又隨著商業模式的變遷形成新的形態。“本地生活服務”本質上就是廣告,對於擁有流量的平臺來說,只要有利可圖,掀起一場大戰又如何?抖音在“本地生活服務”的強勁增長直接威脅到了美團的核心利益,這場戰役最終難有大贏家。
美團的護城河
美團成立於2010年,恰逢移動互聯網進入3G時代(以及智能手機的快速滲透),這是PC互聯網向移動互聯網進行大規模陣地轉移的關鍵節點(微信就是在2011年推出的)。移動互聯網(帶寬增大)和智能手機提供了全新的基礎設施,並由此產生了新的商業模式,而新的商業模式在極大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其中最核心的莫過於人與人、人與事、人與物的連接方式和互動程度。
美團以團購切入互聯網服務領域,經過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千團大戰”後與騰訊投資的大眾點評進行戰略性合併;隨後在與阿裏系扶持的餓了麼在外賣領域的對決中確立其霸主地位。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在巨著《隨機漫步的傻瓜》中提到的未然歷史(過去可能發生但沒有發生的事)告誡世人,美團的勝利並非是後視鏡中的必然事件。坐穩外賣業務龍頭之後,在網路效應與資本的加持下美團開啟了狂飆模式。自2015年與大眾點評攜手後,營業收入從40億元飆升至2022年的2200億元,八年時間增長了55倍,代價為527億元的經營虧損。
在互聯網時代,諸如騰訊、阿裏、百度、京東、拼多多等一眾企業,其本質形態都是“免費+收費”的流量型平臺(對用戶免費,對用戶的對手方收費),其核心在於連接:阿裏系(主業)連接了製造商與製造商(B2B)、廠商與消費者(B2C);騰訊的微信和QQ連接了人與人。美團作為連接器(2021年之前的戰略定位是“Food + Platform”),以連接服務商和消費者為起點;在2021年將戰略定位提升為“零售 + 科技”,意味著美團業務的擴張:為C端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服務(橫向擴充品類),為B端提供供應鏈和管理服務(縱向深度賦能)。
騰訊,作為國內社交軟體的霸主,憑藉超高的用戶轉換成本作為其護城河,圍繞著首屈一指的流量開疆拓土。美團同屬流量平臺,其核心競爭力是700萬的“運力”和其轉換成本。更本質地理解是:社會(經濟分佈)的金字塔結構才是當前美團的護城河。勉強地說,雖然送外賣被貼上“底層”的標籤,但美團實實在在提供了大量的靈活就業崗位,為塔底階層的勞動力提供“開源”的選擇。而“運力”的轉換成本之高,與另一個靈活就業崗位相比即可理解:存在許多身兼多個APP的網約車師傅,但幾乎沒有一位能夠多平臺同軌的騎手先生/女士,不同的群體面臨的生活成本和選擇是跳躍式的差距。
流量的共鳴
美團憑藉龐大的運送網路,利用外賣業務產生強大的網路效應(由“運力”產生的便利性吸引更多的用戶,更多的用戶吸引更多的商家,更多的商家提供更多的選擇,更多的選擇吸引更多的用戶...),為其平臺提供雙向的增量流量,而量積累到能產生規模效益的時候引發質變,在2C的業務上衍生出2B業務(商家數量的持續增長,美團推出了快驢為商家的供應鏈賦能)。
任何依靠流量的2C業務,最容易變現的路徑就是廣告,平臺的流量越多、黏性越高,其經濟價值就越大。美團的業務基礎就是廣告,或衍生、或變形。美團的業務由“核心本地商業”和“新業務”兩部分構成,前者貢獻超7成的營收,又進一步的分為“餐飲外賣”和“到店、酒店及旅遊”兩個板塊。商家入駐美團從本質上就是通過平臺為自己打廣告,而美團一方面撮合交易收取提成構成其“傭金”業務,另一方面又對有需求的B端收取額外服務費用成就其“線上行銷服務”業務。
對平臺型企業而言,流量就是經濟(更重要的是流量幾乎沒有邊際成本)來源,將流量有效地轉化為經濟收入才能形成商業模式的閉環,流量的共鳴就產生了:變現(自媒體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聚集了大量粉絲之後就開始尋求變現)。
“本地生活服務”硝煙已起
流量的核心屬性(幾乎沒有邊際成本)促使其不斷地尋找變現路徑以提升流量的經濟價值(例如,不考慮用戶體驗的話,騰訊在朋友圈打兩個廣告和一個廣告的成本幾乎是一樣的)。那麼從理論上,只要有利可圖,流量變現幾乎無“跨界”一說,出行業務一超多強的局面或許將在“本地生活”複現。
抖音擁有8億的日活躍用戶量(僅次於微信),正所謂“流量在手,天下我有”,僅通過3年半的時間,抖音電商的成交額就達到驚人的2.2萬億元(約當1/4個淘寶,1/2個拼多多)。而抖音進軍“本地生活服務”不僅僅是因為其高頻和剛需,更重要的是“暴利”。通過解剖美團的業務構成(2021年)發現:(1)“餐飲外賣”營收963.12億元(營業利潤率僅6.41%),其中“餐飲配送”營收542.04億元(虧損139.79億元);(2)“到店、酒店及旅遊”收入325.3億元(營業利潤率高達43.32%),“傭金”和“線上行銷服務”是核心利潤來源。
“線上行銷服務”的本質是廣告,而“傭金”則是廣告(見效)帶來的附加值。既然本質是廣告,那麼擁有巨額流量的抖音就能做,甚至對抖音而言不存在任何門檻:平臺在B2C模式之下充當著連接器的角色,對B端來說需要更多的曝光量來提升銷量從而帶動規模產生更高的經濟效益,而對C端來說能夠擁有更多的選擇權以及平臺爭奪份額而產生的性價比。
抖音在2020年以“團購”業務切入“本地生活服務”領域,GMV(總成交額)從2021年的110億元飆升至2023年的3100億元,若按照10%的變現率約310億元的營業收入,相當於15%的美團核心本地業務;並且,抖音不僅對2024年的“本地生活服務”定下了6000億元的銷售額,還要提升該業務的盈利能力。
對於美團而言,“本地生活服務”市場規模雖然大,憑藉其“運力”網路在時效性上佔據優勢,以往的對手幾乎都難以撼動其地位。美團面對這場無可避免的戰役,競爭難度將遠超過往。抖音的目標是既要增量又要增利,那麼在C端無溢價的背景下只能向B端下手,而B端在多平臺之間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抽傭太多或其他服務費用太高侵蝕商戶的邊際利潤甚至導致商戶增收不增利的話就留不住商戶),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加商戶的數量發揮規模效應(打廣告嘛,一個也是打,兩個也是打),這就意味著要搶奪這有限的資源,直接向美團宣戰。
戰爭從來沒有大贏家
抖音強勢進入“本地生活服務”勢必與美團兵戎相見,但自古以來,戰爭從來就沒有大贏家。從“本地生活服務”的價值鏈上看:平臺的利潤幾乎只能向B端索取,但是B端從本質上也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平臺利潤空間的大小取決於其為B端帶來的邊際利潤,而B端的邊際利潤就是其通過銷量的增加攤低其固定成本。美團和抖音在“本地生活服務”的競爭,不可能無限地創造賦能所帶來的增量價值,也就無法持續向B端索取利潤,最終的結果大概率就是大幅降低“本地生活服務”業務的利潤水準(目前可是43.32%):對於抖音而言,20%的營業利潤率也都是增量;但對於美團而言則必須要依靠大幅增加的量來彌補即將失去的質。
結語:美團也好,抖音也罷,對於消費者和商家而言都是可選消費品,有限的資源在面臨多方爭奪的時候價值會提升,而平臺不可能無限通過賦能創造增量價值,就意味著利潤空間必然會壓縮至傳統業務的水準。